 |
浙商文化 |
| 浙商是近代才崛起,且在學術界上並不響亮的名詞。我曾經探訪過南宋狀元陳亮“義利並舉”的浙中學派的宣導者的故土永康;也曾經到過撥浪鼓之鄉義烏,探究中國最早的市場經濟文化的起源,但一直沒有看到學術界對“浙商”這一概念的論證和闡述。 但如果因此說浙商歷史短暫是沒有道理的。在《史記》記載中,中國最早的大商人,也就是後代商人的鼻祖“陶朱公”範蠡(西元前473年)就是戰國時期越國的名臣。而南宋時期浙中學派的代表人物陳亮提出義利並舉的思想與傳統的重農抑商思想形成了鮮明的對比。18世紀,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與上海口岸的開放更是為浙江商人提供了歷史舞臺。以寧波幫為代表的浙商群體對上海近代化的演進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寧波幫不但在國內,在國際上也留下了很大的影響。甚至有人給予寧波幫“無寧不成市”的評價。現代寧波幫更是湧現了船王包玉剛和香港董建華之父董浩雲等代表。 除了寧波幫以外,浙江許多地方都有著悠久的民間經商的歷史。在義烏,撥浪鼓文化在清乾隆時就已經興盛。而浙江人天生就有一種經商精神。在改革開放之前的“割資本主義尾巴”的特殊時期,溫州、寧波、義烏、台州、永康等地的百姓卻“頂風作案”,而一些地方的領導也對此“心知肚明”。但本書所介紹的只是指改革開放土壤中孕育出來的在市場經濟的商海中搏擊的浙江企業家的部分代表人物。他們中有土生土長的農民企業家;也有國有企業發展與改革中成長起來的國企掌門人;有現代“儒商”和“資本玩家”;還有正在成長的新一代的知識型的企業家。在他們的身上可以看到浙商所固有的市場意識、風險意識和自強不息、吃苦耐勞、不斷創新的精神。 那麼,浙商與其他三大商幫究竟有什麼聯繫與區別呢?經過前面的分析,不難看出,浙商在歷史上就是各大商幫的合作者和競爭者。晉商與浙商交易絲、綢、茶、米;徽商東進蘇杭而至楊帆入海。徽商代表胡雪岩又兼具浙商身份。其代表作——胡慶餘堂更是以歷史見證物的身份留在了杭州;其末代傳人馮根生在承繼其老財東的經營思想的同時演繹了一曲現代浙商的詩篇。總而言之,浙商吸收了以上三大商幫的許多精華,比如晉商的博大寬容的經營胸懷、相容並蓄的經營氣度、求同存異的經營策略和自強不息的經營精神;徽商仁義誠信的儒商文化;潮商的冒險精神和學習精神等等。但浙商之所以能跟隨歷史的腳步不斷發展,有其自身獨特的特點。 首先,無論晉商、徽商,其本質都是官商;而浙商是“民商”。晉商與封建政府緊密相連的關係;徽商的“商而優則仕”的思想都註定了它的歷史局限性與內在動力的局限性。而浙江經濟從本質特徵上說,是一種“民本經濟”。所以,“浙商”與“晉商”,“徽商”的區別,前兩者如果可以稱為“官商”的話,“浙商”應該可以稱為“民商”。 如果說,“官商”是封建時代的產物,那麼到了現代的市場經濟時代;其經濟界的主角也必然要由“民商”來扮演。而所謂“自強不息、堅韌不拔、勇於創新、講求實效”的“浙江精神”,也正是“民商”的精神。悠久的歷史和淵遠的文化背景,以及“百工之鄉”地利,使得這個“百工之鄉”成了“百姓經濟”肥沃的土壤。這也使得浙江在全國都以國有企業為主導的時候就能放手讓成千上萬的“民商”自由搏擊,使得浙江的民營經濟一枝獨秀。這也正是浙江民營經濟三分天下有其二,各項指標均居全國第一的原因。 “浙商”與“晉商”、“徽商”的第二個區別在於產業發展的能力。“晉商”雖然形成了商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的兩大勁旅,但最終並未出現商業資本向產業資本轉化的趨勢。而“徽商”由於“官本位”的思想沒有致力於產業投資。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浙江區域經濟的基本特徵即可概括為“簇群經濟”。這是以專業分工的高度細化和集中化為特徵產業經濟的。 浙江專業化產業區的發展孕育了一批又一批的浙江商人。近年來,浙江各地湧現了成百上千個專業生產的專業村、專業鎮。其中產值超億元的特色產業區500多個,而且,浙江的產業群越來越大,以至許多專家把浙江的專業化產業區與義大利的產業區相比較。記者在採訪中常常聽到企業家朋友這樣的豪言:“為了實現產業報國之夢,國外公司拿兩倍、三倍於我的企業資產的現金在我的面前也決不動心。”“我們的未來是在非常尖端的產業裡與世界巨頭對抗,在對抗中我們也許會失敗,但我們仍然要參與這種對抗……”而許許多多的“魯冠球”、“南存輝”、“王建沂”們正在努力著,迎接著國際產業大轉移。而當前發達國家正加緊把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市場經濟十分活躍的浙江地區正成為外商首選的對象。因而,浙商群體正自覺地將打造“世界工廠”作為自己努力的目標和方向。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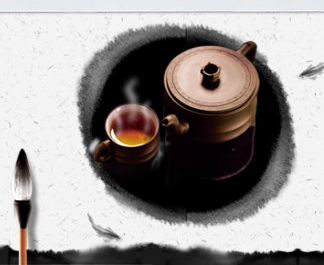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