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論祭祀詩反映的南北文化 |
| 提要:古人雲:"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祭祀和征戰,反映兩個現實層面問題:直接的交戰,決定國家存亡;間接的祭禱,透露生活安定的願望。祭祀,是種古老的儀式行為,它的形成,與環境的挑戰有密切關係。遠古先民對於自然界的事物不甚瞭解,環境的一切變化,他們只能抱持慎懼的心態,進而產生崇拜、祈求自然的行為。不論是華夏民族,抑或蠻夷狄戎,均曾處於對世界無知的蒙昧階段。中國詩歌的兩大源頭--《詩經》與《楚辭》,為南北文學的代表,兩書收集許多祭祀詩歌。祭祀詩除了文學價值以外,承載的文化意涵更不容忽視。本文以《詩經?周頌》與《楚辭?九歌》為範圍,透過祭祀儀式的探索,一窺南北文化體現的歧異。 關鍵字:周頌 九歌 祭祀詩 文化 詩騷 祭祀是遠古時代諸民族共同的儀式行為,藉由祭祀活動,向上天、萬物或祖先,表達內心欲求,期許生活美好,甚至祈求國家的安定。各民族在相同的需求上,進行不同的祭祀活動,整個過程中,物件抉擇、表現形式、祝禱語詞、音樂歌舞等等,往往表現該族深層的價值判斷。因此,祭祀活動不僅是單純地拜天求神,儀式底層下,也隱藏著不同的文化體現。 《詩經》與《楚辭》為南北文學之祖,《周頌》與《九歌》同為祭祀詩,風味卻大相徑庭,這種歧異,除了文學手法運用巧妙不同外,植根於社會的深層文化意識,亦扮演重要角色。《周頌》與《九歌》,正是我們瞭解周、楚文化風貌的起始點。 一、《周頌》與《九歌》的祭祀對象 夏商周三代,對祭祀活動十分重視,尤其是殷商,可以說是個鬼神盛行的年代。依據祭祀的物件分類,古代祭神大致分為天神、地礻氏、祖先三大系統,商周兩代,三大系統的重要性略有變化。上帝、祖先、日月星辰、山川百物,殷人皆祭拜,祭祀的典禮名目繁雜,祭品種類眾多,甚至還有以人為牲的習慣。時移西周,祭祀之風本質漸易,周人祭祀的物件,承續殷商而來,拜上帝、祖先、日月星辰、山川諸物,然而,他們的鬼神觀念,仍與殷商有別。周朝更著重祖先的祭祀,因此,王暉稱周朝是個"尊天保民,天人合一"的時代(1)。 陳夢家認為古代許多的民族,普遍存在"祖先崇拜與天神崇拜逐漸接近、混合"的現象(2),周代的祭祀物件中,祖先神具有重要的地位。在甲骨刻辭或者史料文獻中,詳細記載周人祭天拜鬼的儀式,以《周頌》為例,卅一篇中告于祖先的詩篇比例達58%(3),《周頌》為天子舉行郊廟祭祀之舞曲,可見祖先地位在周代的崇高。另外,《周禮?大宗伯》所記的十二吉禮中,宗廟之祭有六,祭天、祭物反而少於祭祖。祭祖的典禮繁複隆重,態度莊嚴,絲毫不可有怠慢之處(4),在在說明了祭式儀式的重要性。 綜觀《周頌》,所祭之祖有文、武、成、康、大王、後稷等,參與祭典活動之人,除了國君以外,諸侯、外族也擔任助祭工作。祭祀的祝詞,以描述先王功德盛美,子孫宜信守師法之形式居多。《周頌》有部分篇章,如《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歸屬農事詩,尤其是最後兩首詞,敘述農事過程十分詳細完整,為最佳農業史料。雖然它們是農事詩,卻不悖祭祀宗旨。例如:"于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臣工》)"為酒為醴,畀祖妣,以洽百禮。"(《豐年》、《載芟》)農事詩更換不同方式,以報祭、祈谷、籍田為祭祀內容,上告于祖先、上帝,希冀來年亦能豐收,主題明確,依然以祭祀為最終目標。 除了祖先崇拜,《周頌》亦有對"天"表示崇敬的詩,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維天之命》)"昊天有成命,二後受之。"(《昊天有成命》)祀天之典,是非常隆重的事情,依照上述引詩,可知周代崇敬上天,但是,天不是永不可抗的力量,因為上天仍得聽從人民的聲音。天和人的距離,似乎已經拉近;天與人的關係,因為周人思想的改易,而產生微妙變化,關於思維方式的問題,下節將進行析論。 位居南方的楚國,流傳一套優美浪漫的祭神樂曲--《九歌》,它原是祭神樂曲,經屈原改編,文辭麗贍。《九歌》共有十一篇,分祭不同神明,除《國殤》悼人鬼(5)、《禮魂》為送神曲以外,其餘均為自然神,而且,也分屬天神、地礻氏系統。各篇章所祀何神,歷代的說法分歧,大致上《東皇太一》是楚人的上帝,為天神中最尊貴者;《東君》為日神;《雲中神》是雲神;《湘君》、《湘夫人》是水神;《大司命》、《少司命》為司命之神;《河伯》是河神;《山鬼》為山神。楚公室特重祖先與河川(6)。現今《九歌》僅有十一篇,並非當時祭歌全數,它是經過屈平篩選後流傳下來的代表歌曲。觀《九歌》中的自然神,水神居1/3,屈平為楚國貴族,意味楚公室重河川祭典的事實。 《國殤》是唯一祭人鬼、悼陣亡將士的樂歌,因主題的傷痛,歌頌方式與其它諸神大不相同。透過描述戰爭激烈、國軍勇猛奮戰來表達敬意,雖然馬革裹屍,仍可歸列鬼中英雄。《國殤》悲壯的筆調,與《周頌》歌詠文武先王的美、凝重,呈現強烈的對比。雷慶翼認為《國殤》是國家的祭典,若所言屬實,它與《周頌》便為同等級的典禮,兩相比照下,南北文化的區別昭然若揭,《國殤》的情感意識奔放,《周頌》內斂穩重,實與兩國深層的思想質素,有密切關聯,這也是以下所要探討的重心。 二、《周頌》與《九歌》的思維模式 周文化強調以人為中心,無論是探討人與自然、人與神或人與天的關係,皆是以人的角度為基點,用"人"審視一切,所有的事物均沾染人的特質。"天人合一",的確是周朝獨特的思想,在這點上,與殷商時代對天的看法全然不同。殷人以為天命將永遠不離子孫;周人由殷商覆亡的教訓,體會出天命靡常,恒無一定的道理,上帝鬼神是否佑助周王朝,並非上帝自己的決定,應該憑恃百姓的意志決定。天和人在某種程度上是相通的、互相影響的。神明必須聽從生民的聲音,對於統治者而言,他們要費心力的地方,在於敬德保民,而非天天祭拜神明。是故,《孟子?萬章上》引《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透露出天與人的距離不再遙遠。《周頌》裡祖先崇拜的之例豐富,關於這點,常金倉以為祖先崇拜受到政治因素的制約,他以希臘為例,說明希臘人跨入文明社會後,執政官和元老院的政治權力,是由氏族社會選舉出來,祖先對於得權,並沒有直接功勞,他們不必感謝自己的祖先。中國的政權,往往用武力建立起一個以家族為核心的勢力,因此,君主必然得懷念、感激先王的功業盛德,這就刺激祖先崇拜的風氣。(7)《國語?魯語上》雲:"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明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這段話似乎與常氏的說法有雷同處,當上帝、神明或祖先無法捍衛百姓時,人民便不願意去祭祀礻也。此說雜揉功利意味,與希臘祖先崇拜沒落之因是相容的。 範文瀾在《中國通史簡編》中,曾提出的"《詩經》是’史官文化’,《楚辭》屬於’巫官文化’"之說(8),試圖解釋南北文化的差異。魯迅以為中國神話之不發達,是因為華土人民,重實際黜玄想(9)。李澤厚、劉綱紀也說北方神話遜於南方,主要關鍵在於北方較早進入階級社會,"史"取代"巫"的地位(10)。魯迅由外在環境角度,厘出中原文化特徵,自有其道理,然而,歸因於環境困窘的事實,便能推演出中原以人為主的文化意識,論點過於單薄。范、李、劉三人的詮釋,足以化解此問題的癥結。周代繼殷而起,周人成功地扭轉殷商每事祭的迷信風氣,重要的推力是周文化與政治(11)的結合,為了滿足政治需求,使得祖先崇拜得以在眾多祭典中脫穎而出,在天子祭歌的紀錄--《周頌》中,國君向先王祭禱的篇幅之豐,正是祖先崇拜盛興的證據。政治力的介入,祭祀儀典被設計成等級分層式,依《禮記》的記載,天子、諸公、諸侯、大夫、士,無論祭祀時間、品類、數量,各有規範,絕不逾矩(12)。在重重禮法制度之下,典禮的進行必然謹慎,《周頌》是官方的祭祀詩,它呈現的祭祀文化和《九歌》會如此截然不同,政治力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 楚國祭祀文化的特色,一是神明數量眾多,二是不排斥他方神明,人神交融的浪漫意境,更是楚文化的奇葩。楚文化之所以擁有特別的浪漫情調,外在環境(熾烈的巫風)的確發揮不小的影響力。如《呂覽?異寶》曰:"荊人畏鬼而越人信礻幾。"元稹《賽神》:"楚俗不事事,巫風事巫神。事妖結妖社,不問疏與親。"均指出了楚地信仰鬼神的普遍性。《九歌》的書寫方式,各篇不盡相同,不過,這些神明的形象總是鮮活動人,仿佛人間的投影。雷慶翼認為《九歌》是"俗祀"與"典祀"的組合,但《九歌》絕大部分內容為想像的境地,孰為典祀,孰為俗祀,區分將有困難。撇開典俗之爭,《九歌》醞釀於民間已是公認的事實,因此,它與《周頌》在儀式本身的嚴謹度上,自然不可相取比況。巫風的流行與上述魯迅外在環境的論說,同樣屬於客觀原因,尚不足以澄清楚祭祀文化的形成。或許,我們必須考察楚國歷史特殊的進程,找出它與北方相異之真正因素。 楚國在周成王時立國,草創時期,客觀條件極為險惡,甚至到莊王滅庸後,楚人的生活仍十分艱苦。《左傳?宣公十二年》曾雲:"訓之以若敖、蟲分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若敖、蟲分冒貴為領袖,依舊得辛勤地和百姓一起開發山林,可想見其物質生活的困窘,而領袖其實並未掌握太多權力。楚國的歷史進程中,宗法觀念並不發達,國君的繼承不一定依循嫡長制,《史記?楚世家》載:"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望祭群神,請神決之。"由此可知,嫡長繼承的觀念並未深烙于楚人腦中。在土地管理與財產分配方面,楚人設縣,行祿田制,封建必須奠基于宗法的親親關係,楚人宗法觀不穩固,並未採用封建制。慮及時代之因素,也不允許楚國實施宗法制,春秋戰國時期,社會紛亂,戰爭紛仍,整個時代所面對的難題是"周文疲弊",周朝所制定的禮樂規範,不達於世,促使眾多的思想議論林立,終極目的便是為時代提供一條新路。在禮法鬆散的年代,楚國若實施親親宗法制,勢必窒礙難行。 李澤厚與劉綱紀精確地點出,南北文化的區別在於:"氏族社會風習的大量存在,使得楚國及其文化不像北方那樣受著宗法制等級劃分的嚴重束縛,原始的自發產生的自由精神表現得更強烈,對於周圍世界更多地是採取直觀、想像的方式去加以把握,而不是進行理智的思考。"(13)《九歌》和《周頌》的祭祀文化,會呈現如此大的差別,根本關鍵即深層的思維模式的差異。北方受到政治力的影響,宗法禮治主導了祭祀文化,南方因為歷史的發展,對於人事、禮教缺乏深切體認,思維方式不被繁瑣禮樂規矩束縛,再配合上外在巫風的客觀條件,南北兩方便走出不同的祭祀風格。 《國語?楚語下》有一段紀錄:"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天子遍祀群神品物,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禮,士、庶人不過其祖。"此段話說明楚國祭祖亦分層級。春秋戰國時代,周天子名存實亡,對於諸侯國沒有約束能力,該項規定,已被打破,楚風淫祀情況為普遍之事實。 (14)《九歌》反映的年代是戰國時期,戰國的文化較西周早期(《周頌》的年代)活潑開放。是故,《九歌》的整體風格也相對地奔放活潑。限於歷史的潛在因素,導致楚國無法深刻瞭解人文精神,巫風彌漫整個社會,《九歌》的神明,皆是極度美化,任想像馳騁的產物。 三、《周頌》與《九歌》的祭祀功能 周文化的典型特徵,就是人文精神的激昂。在周密的禮教規範下,宗法觀念、封建諸侯,成為維繫社會和諧最重要的力量。這股政治涵義濃厚的力量,滲透到宗廟祭典,直接地影響祭祀行為最終的目標。趙輝對此儀式之目的,作了嚴厲的批判:"中原人進行祭祀的目的,並不在鬼神本身,而在於借對鬼神的祭祀,去維護封建統治,防止老百姓犯上作亂。宗教在中原人那裡,已完全變成一種愚弄人民的統治工具(15)。"關於祭祀是否為愚民工具,在此不作任何評論,誠然,該言一針見血地點明祭典的舉行,不過是基於政治需求所為的必要工作。周代祭典的重要功能,不僅僅落實于人世層面,它還提高到政治層面。前文談及思維模式的運作,便是政治力量的介入牽引。《周頌》的祖先崇拜,蘊含著深刻的政治目的--強化宗法與等級意識、懷柔夏殷遺裔、鼓舞民心努力耕作。 (一)宗法與等級意識 周禮設計的宗法制度,由血緣基礎上建構而成。無數的大宗、小宗,由個人到家庭,再延伸至國家,形成綿密的人際網路。王室舉行祭祖大典,鞏固血脈相連的宗法精神。《禮記?祭法》雲:"設廟祧壇土單而祭之,乃為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土單,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廟祧制度的安排,親疏關係、父子之倫是主要的設立標準。周王統治的手段--分封諸侯,必須依賴等級制度的規定,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庶人祭於寢,就是一種上下有序、層級分明的表現。每舉辦一回祖祭,便強化一次宗法、等級意識。 (二)懷柔夏商遺裔 周人以武力奪得政權,分封夏之後于祀,殷之後于宋,自行其正朔服色。《周頌》中有不少篇章,談到諸侯助祭典禮,如《振鷺》雲:"振鷺于飛,於彼西 。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詩序》:"《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二王,即夏裔和殷裔。李樗《毛詩李黃集解》:"二王之後不純臣待之,故謂之我客。"敬稱為客,表示周人以客禮相待,希望政治立場上大家都能和諧。 (三)鼓舞民心努力耕作 後稷以農開國,農事耕種為國家糧食來源,因此,籍田之禮總是十分隆重。 《良耜》詳細地記錄耕作過程,與豐收之喜:"良耜,亻叔裁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獲之扌至扌至,積之栗栗。……殺時牡,有扌求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詩序》:"《良耜》,秋報社稷也。"詩中呈現一幅農人努力耕作的畫面,經過一年的辛勤,秋天得到大豐收,國家舉行盛大的祭典,將豐年之悅上告先祖,祈求來年農事亦能順利。 《九歌》最高的天神為東皇太一,全詩鋪敘典禮的喜悅、熱鬧的場景,極言祭品豐盛、樂舞多彩,神明喜樂安康。只是,福祉的具體內容並未明白說出。 《東君》,祀日神,歌詠太陽的光輝和功德。東君的形象呈陽剛之美。礻也駕著馬匹縱橫穹蒼,散發和煦陽光,最後還道出"舉長矢兮射天狼",展現日神英武風貌。《雲中君》,祀雲神,亦有祭雷雨神、月神之說。雲在天空漂泊無定,晴雨變化,風雲莫測,百姓求禱風調雨順,以利生產。 《湘君》、《湘夫人》、《河伯》皆為水神,前兩首詩歌風格特別,互相呼應,描述水神之間情感的忠誠懇摯,詩歌著重于水神等待對方的過程與心境,祭祀主旨不甚昭顯。《河伯》即河神,"沖風起兮橫波",點出河川驚濤巨浪的特徵。大抵祭祀河川水神,不外乎求雨、驅瘟、消災等原因(16),雖然《湘君》、《湘夫人》、《河伯》並未明說祭祀目的,但應該可在上述諸因中找到答案。 《大司命》與《少司命》各有專職,一般認為大司命主壽夭,少司命的職務說法分歧,或是主緣之神,或是子嗣神,或為災祥之神。九州的人口眾多,生死壽夭全掌握在大司命手中。祭祀大司命,求神靈賜歲,延年益壽,減低生死無常的恐懼。清代王夫之主張少司命為子嗣神,雷慶翼加以補充,司命,主宰生命,大司命支配生命長短,少司命掌握生命有無,祭拜少司命,希冀獲得子孫(17)。 《山鬼》,祀山神。她"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是一個美麗的女神。全詩側重於山鬼的感情世界,形象的高潔,與民間原型全然不同。祭祀山川神礻氏,是源流久遠的習俗,古人認為高山峻嶺,是百神聚集處所:"朝發軔於蒼梧兮,夕餘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離騷》)縣圃、靈瑣在昆侖山處,蔣驥《山帶閣注楚辭》曰:"《山海經》昆侖山帝之下都,面有九門,百神之所在,故曰靈瑣。"屈原欲往縣圃、留靈瑣,為得是向天帝訴苦。祭山之祀,能得神佑,就如同得上帝群神之助。 《國殤》,贊為國捐軀的勇士。它的性質似《周頌》,以歌詠頌贊方式,安慰亡魂,也激勵生者的鬥志。《禮魂》是首送神曲,作為祭典最後的完結。 《九歌》中遍祀眾神,所求願望植根于現實,求子嗣、求雨水、求年壽等等,均是普遍性、共通性的需求。《九歌》求索特徵,與《周頌》不盡相同。縱然《周頌》述農業的詩,也是以求豐收為主要目的;《九歌?雲中君》暗喻滅秦之志,傳達的心願層次高及國家情仇,不可否認地,這些例子畢竟少數。《周頌》絕大部分是歌功頌德的祭祀詩,關懷的問題是國家政治的等級,周王祭祖,自我勉勵,希求國家一切平順,實踐敬德保民。《九歌》以祀自然神礻氏為主,既然原為民歌,人民關切的問題不離自身的範圍,拜山祭河,是基於滿足普遍層面需求。換言之,南北祭祀目的之出入,和兩方的思維運作有緊密關聯。 四、《周頌》與《九歌》的音樂歌舞 頌,為宗廟樂歌,祀神之詩。阮元《釋頌》一文,以為頌就是容,歌而兼舞。關於頌具備音樂與舞蹈性質,在學界已成定論。不過,《周頌》中直接敘述歌舞場面的資料,僅有兩首:"鐘鼓口皇口皇,磬將將。"(《執競》)"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崇牙樹羽。應田縣鼓,罄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口皇口皇厥聲,肅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有瞽》)兩詩所用的樂器,鼓類樂占40%。另外,《維清》、《時邁》、《絲衣》也是樂歌。 周公制禮作樂,使國家步上禮治道路,周代的音樂、舞蹈,《三禮》詳細實錄之。周代的用樂程式,可分成祭祀前、祭祀中、祭祀後三階段。祭前必須用鼓徵引學士,以金奏迎客;祭祀中,則登歌(升歌);結束時,則歌徹。典禮成,以金奏送客,再宴饗賓客。(18) 《周頌》是典禮中所歌頌詠舞的祭曲,如《禮記?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礻帝禮祀周公於大廟……升歌清廟,下管象。"頌之始《清廟》,即登歌所唱的歌曲,《禮記?樂記》雲:"《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矣。"《清廟》節奏緩慢,聲音舒長,並非美妙輕快的音樂。《》按《詩序》說法,是礻帝大祖大詩。依《禮記?小胥》雲:"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鄭注:"於有司而歌雍。"《》通常是祭畢而唱的歌曲。《清廟》與《》顯著的區別,在於前者無韻,後者隔句押韻。 祭祀儀式,除了謳歌吟詠先人烈德,舞蹈的助禱也一大特色。周朝的舞蹈,有大、小舞之分,《武》即是一種大舞,《周禮·大司樂》:"乃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詩序》認為《武》便是大武,《武》是專祀祖先的舞詩。小舞,是童子必習舞蹈。《禮記·內則》:"十有三年,學樂論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禦。"鄭覲文《中國音樂史》指出:"象為文舞,其詩為《維清》之章。《勺》為武舞,其詩為《酌》之章。"《維清》原祭文王,《酌》祀武王,後來列為學校教學科目,是未成年兒童應習功課。 國家級的宗廟祭典,君主是最重要的"參與人",祭祀中,歌舞、音樂齊放,肅肅雍雍,貴為領袖,必須擔負帶頭娛神責任,親身跳舞祭祖,《禮記?祭統》:"及入舞,君執干戈戚就舞位,君為東上,冕而 幹,率其群臣,以樂皇屍。" 由天子率臣以舞悅鬼神,才是祭祖之道。《禮記·樂記》有段故事,記魏文帝問子夏古樂與新樂之別,子夏答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屍……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音樂舞蹈,終極目標是固倫常,倫理觀念深植民心,政治統治於焉穩固。 北方《周頌》,歌舞並重,南方《九歌》,亦複如是。相形之下,楚國的樂舞場面,活潑熱鬧,奔騰昂揚。《九歌》最顯著的特徵是浪漫的、情愛的氣氛濃厚。左天錫曾雲:"實際節歲有時兼祀神,而祀神後,又常在相歌舞以成配偶。並且歌以樂神的歌,又多為言男女之情。"(19)《湘君》、《湘夫人》正是采歌詠相思、期待依人的方式以娛水神。 楚國祀神儀式,從頭到尾,沉浸於一片歌舞聲中,《九歌》的想像空間十分地寬敞,巫 盛裝扮演各種鬼神,搭配喧天的樂器演奏,舒喉高歌,拂袖長舞,展現虔誠的悅神敬鬼心意。《九歌》所用的樂器種類,以鼓伴奏居多。楚國祭祀樂器以鼓為主,西周以鐘磬為主,因為戰國時代,禮崩樂壞,輕鬆活潑的鼓樂、管樂、弦樂,盛極一時,楚樂重鼓,反應歷史轉變的情形(20)。依據楚墓和曾墓所出土樂器,計有編鐘、編磬、鼓、瑟、琴、竽、排簫,以地下文物與《九歌》對照,大致是吻合的。 對於巫巫見的舞姿,《九歌》言"偃蹇"、"連蜷",偃蹇形容舞姿宛轉,伸屈自如;連蜷形容舒曲回環之貌。嬌小玲瓏的身軀,跳起翩翩巫舞,自然會產生偃蹇、連蜷的曲線律動美。上海博物館有幅刻紋燕樂畫像,舞人的形貌特徵為袖長、體彎(21),由此可知,楚舞尚宛轉曲環,婀娜動人的舞態,不僅神靈喜歡,觀者也忘歸。 祭禮物件不同,所跳之舞即異,譬若河伯為河神,巫巫見跳的舞蹈是"乘白黿兮逐文魚,與女遊兮河之渚";山鬼,山中女神也,容貌姣好,服飾華麗,女巫裝扮成"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做出"采三秀兮於山間"的動作。《九歌》充滿著肢體語言的動態美感,它的浪漫是思維所賦予的表徵。反觀《周頌》,面對的是功業彪炳的先公聖王,為了表示子孫的無限景仰,只好規矩地歌頌祖先,末以自我戒慎作結,它所能發揮的想像空間,遠不如奠基於民間的《九歌》。在用樂方面,《周頌》沉鬱節度的風格,宣導金聲玉振的鐘磬禮樂,顯然與楚國南轅北轍。 歷來,對於周楚文化發生的可能,歸因於外在環境的影響,此說固然無大不是,然而,卻不足以涵蓋說明南北文化的種種異途。根據前面的推論,筆者以為周代實施的宗法、封建制度,挾帶而成的政治力量無遠弗屆,因為政治力的干涉,使得具有文化意涵的祭祀活動,沾染倫理色彩,祭祀內容、用樂狀況,無不是著眼於倫常。為了強化人民的等級、血緣觀念,祭奉先公先王,必須從歌頌讚揚偉業聖德的角度出發,讓全體群眾肅然嚮往。藉由禮遇夏商遺族,表示有周雍雍大國的包容力量。 相對于北方中原,南方被視為蠻夷之地,文化落後,禮教不行。考察《九歌》所保留的詩篇,其實遙遠的南方楚國,非但擁有自己的文化體系,並且,該文化氣息與北方截然有別。楚國歷史的發展過程,走的和西周是不同的一條路線,它沒有殷鑒可尋,周代承襲殷禮,進一步改造了它,讓一切的禮樂制度更加齊備,國家按禮教治理,自能運作順暢。楚國欠缺這種文化傳承,它的周圍幾乎都是信鬼迷巫的民族,因此,楚無法像周朝對"人"有如此深刻的體會,楚人祭祀祖先,但也可以違背祖靈,周人祭祖,矢言賡續、發揚。楚人好祀,天地山川,無所不拜,《九歌》中的神靈,多采多姿,喜怒哀樂,形於顏色,飛天遁河,隨心所欲,巫巫見歌舞,通宵達旦,盡情而歡,在在體現楚風高昂自由的特質。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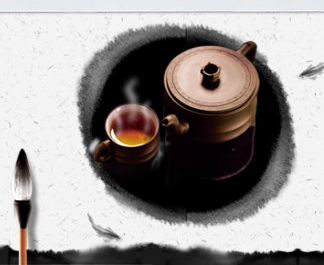 |